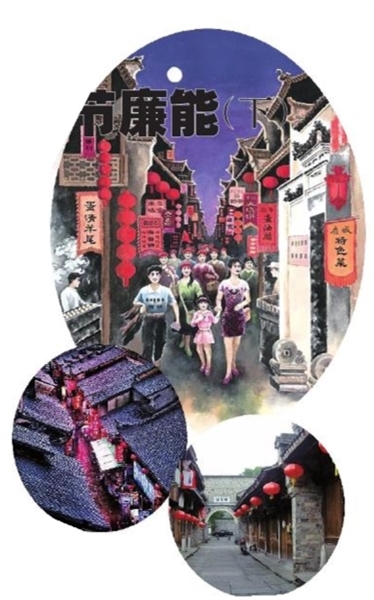万历三十六年(1608)王士昌先后任刑部员外郎、礼科给事中、大理寺署寺事右寺丞。在任期间,他又遇到了一件与太子有关的大案——梃击案。
梃击事件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当天傍晚,一个蓟州平民张差,手持枣木棍,竟然从东华门直奔深宫内廷,还闯进了本该防守森严的朱常洛住所,直到慈庆宫前殿屋檐下才被捉拿。事发后“举朝惊骇”,负责审问此案的“浙党”官吏说张差是个疯癫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在提审时,诱使张差供出幕后主使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因此,朝中东林党人坚决要求彻底追究。
王之寀带头上疏请求彻查,但奏疏上达后,被留中不发。许多正直大臣都站在王之寀一边,认定梃击案完全是在郑氏家族谋划下的有组织、有预谋的重大案件。审理此案的王士昌也踊跃上疏,一一指出案中种种疑点:一是“夫至失心如躩兽然,遇物则击,岂能择地而施,待人而欧,待时而发耶”?张差的行为表明他不可能是疯子;二是“方其执棍于街市之中,从容于后宰之入,何竟无一人觉察”?张差在深宫内竟如入无人之境,实在非常蹊跷;三是“直至宫门,乃始逞技耶”?所有一切,似乎都是精心策划安排的,种种疑点必须澄清。疏言还大胆指出万历“虽念念止慈,然弥文煦噢之间,多不慰人望”,既不及时安排太子读书,导致荒废日久,太子之母王贵妃死后又不好好安葬,很多事情做得非常离谱,“皆出人情之外”,难怪举朝上下惶惑不安,希望万历好好读读并妥善处置王之寀的疏言,使法律得到伸张,释疑得到消除。但万历帝因为这是家事,而且事涉郑贵妃,不想深究,决定把张差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秘密打死,草草了结这桩大案。
于是,宫廷中上演了一场非常可爱的戏码。万历召集辅臣并六部五府、大小九卿、堂上官并科道官会聚文华门,想要彻底了断此事,以澄清满朝上下的质疑之声。他在群臣的屡屡谏逼之下,“天语谆谆”地解释自己是如何爱自己的孩子,之所以迟迟不册立有理由种种,不时烦扰着他。如今发生这种事件,几个谏臣竟要兴风作浪,离间父子关系,导致朝廷不像朝廷。万历企图博取大臣们的同情,又想以威势恐吓大臣,将此事囫囵办掉。但刑侍张问达和王士昌还是强烈要求先将涉事的三名案犯处决,“复稍前跪,请得旨,始起”,迫使皇帝问定了梃击案犯。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终究无法得以彻查,此事也成了万历朝的历史疑案。
王士昌的举动得到许多官员和士人的支持,明代东林党首领之一,与赵南星、顾宪成号为“三君”的邹元标曾说:“王禺阳处孟阳、季阳之间,于斗溟则又僧弥,难为兄也,然才各有长。在邑,学为循吏;在朝,学为直臣。”“王禺阳”是指官至福建道御史的临海人王万祚,“孟阳、季阳”是指西晋太康时期著名文学家张载(字孟阳)、张协(字景阳)、张亢(字季阳)“三张”中的兄弟二人;而“僧弥”是东晋王珉(字季琰,小字僧弥),太元十一年(386年),中书令王献之去世,其堂弟王珉接任,时人就称王献之为“大令”、王珉为“小令”。因此,邹元标在这里是先将王万祚的才能在“三张”之间作了定位,然后,又与王士昌作了比较,意思是在王士昌面前只能称小弟了,但两人作为循吏直臣,都堪为楷模。邹元标为人敢言,勇于抨击时弊,其方正耿直的精神和思想广为传颂。王士昌的学问和人品得到这样一位劲节高标、傲岸千古之人的赞誉实属不易。
(三)
剿倭除寇,较早管理经营台湾
万历四十六年(1618)正月,表现优异的王士昌成为封疆大吏,由大理寺右少卿升为督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同时提督军务。
此时,福建正值沿海岛夷内窥声息甚急、倭警频至、江洋大盗横行之际。到任不久,王士昌澄清吏治,清理劣官。查出候选司吏林长春、解官赵承勋与林时中、赵玄同等人一起暗中行贿,制造假印章以多领官府放赈钱粮之事,提请刑部治罪。
九月,又弹劾了“举动乖张、秽迹彰著”,且任用赵若思(即赵秉鉴)等人,导致煽动扰乱事件发生的巡视海道副使韩仲雍。这次弹劾,要从平定水师部将赵若思谋反的事件说起。赵若思原是漳浦县的无赖,身边聚集了一帮轻悍少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福建一带广受倭寇入侵之苦,官方欲增设水师,地方士绅建议将赵若思招为右翼军把总,意在牵制,他因此跟随沈有容参与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五月的东沙大捷。但归正后的赵若思并未改变其“跋扈自喜”的习性,他不仅“威棱如大府”,而且还“约倭为助,许以互市相报”,更派遣亲信以招兵为名,网罗了福建广东一带的江洋大盗和乱民,以致“鼠窃者赴为逋薮,枭张者奉为主盟,无不鳞合”。在海上更是胡作非为,勒索商船,杀戮渔民,收受通倭者的贿赂。有了谋叛之心后,招纳“欲谋据东番(台湾),窃此为夜郎王”的沈国栋、杨钟国为己所用,又联合厦门把总林志武和澎湖把总方舆,进一步壮大力量,企图借袭取占据东番的海盗商人林谨吾之机,“实启兵端,以图叵测”。以博学闻名一时的闽中才子张燮认为,假如他们的计划得逞,必然导致福建沿海永无宁日。
王士昌到任后,赵若思劝说王士昌同意他们在东番(台湾)筑赤堪(又名赤嵌)城堡。王士昌遂命赵若思分别招安林谨吾、沈国栋、林志武、方舆等人固堡守土,这一举动成为明朝福建官府对台湾直接行使管辖权的较早记录,比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还早近8年,可惜中途因赵若思的谋叛而中断,否则台湾的历史可能改写。对于赵若思的谋叛,向来为此临食废箸、提心吊胆的官员早有察觉,但无力对抗处置,他们向王士昌汇报了其中玄机:赵若思筑城管理台湾,其实是想利用官兵的力量实现个人图谋,并且还有密谋攻取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的计划。王士昌听闻后,一面“佯令国栋与若思、志武往谕林谨吾来归,以觇其举止”,一面“密草四檄,一檄纪南路捕林志武,一檄陈玄钟捕赵若思及方舆;一檄漳浦,一檄海澄,俾两县互为应援”。经过周密部署,巧妙诱捕赵若思等人,并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一祸害一方的败类被清除后,“中外人心,因之大快”,“漳人德之,见于缙绅公揭”。张燮亲见此事,认为这是一件“奠国脉、定民嚣、正士风、杜夷衅”的大事,不能没有传记,特意撰写了《海国澄氛记》记录王士昌的功绩。
当时,福建沿海还经常受到倭寇骚扰,王士昌“深念职在防海”,需要一个有经验和才能的将领来统领此事。他想到了曾取得东沙大捷的参军沈有容。沈有容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五月,在东海洋面东沙岛(明属福建长乐县,今属马祖管辖,称东莒)生擒倭寇六十七人,战功卓著,深受士林和百姓赞誉,但却因人妒其功绩而“以浮言拂衣”辞官归里。王士昌屡次写信力促其重新出山,以副将军衔坐镇福州定海卫。沈有容提议在定海(今连江县黄岐半岛)建水标参戎公署,以防卫闽江口。王士昌给予大力支持,是年十月便批准开工修建,如此则使指挥机关前移,变被动为主动。在王士昌的鼓舞下,沈有容组建了闽海第一支海军,也拥有了福建海军史上第一处指挥场所,海防力量大大加强。王士昌的这一举动,引发了当地爱国文士的共鸣,得到了积极点赞。第二年,公署建成,原内阁大学士、福州人叶向高特为此撰写《新建定海参将公署碑》,赞赏王士昌“设险以守其国”的战略思想,称赞此举“为闽土壮干城,为后人规永利,擘画周详,巨细毕举,厥绩尤伟”。曾任太仆卿兼河南道御史的闽县人董应举撰写《总理水军参府题名碑》称赞王士昌“廓落善任”,建公署之举“真足雄镇东而壮江夏者矣”。
万历四十七年(1619)初,福建海上屡屡发生海盗袭击商船事件。福建漳州的李忠(归降后改名李新)号称“洪武老者”,结交泉州同安县渔民首领袁八老(归降后改名袁进),又与粤东龙溪都李忠结拜为义兄弟,占据东番(台湾),过着亦商亦盗的海盗生涯,率领1000多名“沿海奸徒,聚党劫掠商船货物”,“流劫焚毁,势甚猖獗”,甚至攻入甲子城,杀死守城把总金元武,还袭击福建水军,严重影响了沿海商船安全和百姓生活。为了一举消灭这群海盗,王士昌考虑到他们可能会逃入邻省海域,除调动福建海军,由南路副将纪元宪、水标参将沈有容等率官兵征剿之外,还致书广东和浙江两邻省,商讨“互相策应捕剿,以靖海氛”的联合讨伐策略。在沈有容等人率领下的海军主动出击,使这一闽、浙、广三省联合的围剿计划迅速奏效。是年秋,海盗集团袁进、李忠等人驾数十艘大船向西流窜于碣石湾,从甲子洋遁逃到白沙湖,被碣石卫水军包围多日,既迫于广东官兵的追捕,又苦于福建水师的防缉,“计无复之”,只得赴辕门投降。王士昌“宣谕散党归农,方待以不死”,袁进等人立即解散“余党四十余船,被掳六百余人,带领头目陈经等一十七名”,表示愿意报效立功。王士昌因此为二人请旨,收归军前听用,此后二人成为明朝的水师军官,袁进更是由“裨校进大都督”,成为明军的高级将领。
天启元年(1621)四月,倭寇的船只入侵福建彭湖列岛,王士昌又命令地方官兵擒斩贼首黄十二等于虎井屿。
王士昌的抗倭除寇行动,进一步激发了闽中士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海防诗创作的热情:叶向高特撰《中丞王公靖寇碑》,称王士昌“饬戎经武,百凡慎毖,藩臬诸大夫,悉皆民誉,咸展厥猷……公实有大造于我,我其能忘”?茅坤之子茅维作《大中丞斗溟王公莅闽未几,海上剧盗袁进震慑纳款,面缚辕门,公许之降。而乃枭戮其飏去者,海氛一清,颂声四溢。公首唱四律纪之。予适入闽,欣逢盛事,因亦奉和如数云。时己未冬,孟之望》一诗,称此举“波澄瀚海功非细”。徐勃作《海寇袁进横行有年,开府王公谕以威德,投戈归顺,有异志者尽戮之,开府诗以志喜,恭和四章》,有“心怀经略辑绥功,军令分明肃海东。千队旅旗争耀日,一时台阁顿生风”的赞美。官至御史、巡按江右,因属东林党而被排挤辞官的陈一元作《上王斗溟老师开府兼贺诞辰六首》,称“烽烟无警海无波,第一功勋在止戈”。
然而,晚明是一个见不得别人成功的时代,在党争激烈的环境下,功成名就者往往会树大招风,王士昌也像其父、兄王宗沐、王士琦一样,都在巡抚任上提前感受到了政治风波,都在想辞官但没被批准前而被人弹劾。泰昌元年(1620)八月、十月,王士昌在接连遭人弹劾后,回籍听用,从此告别政坛,天启四年(1624)卒于临海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