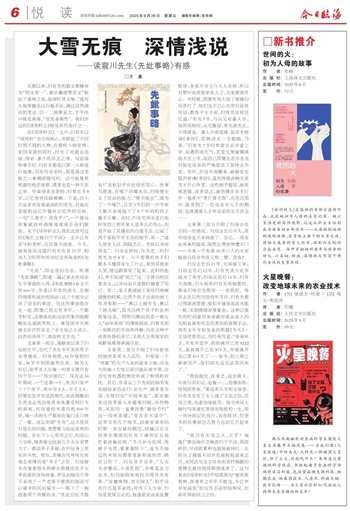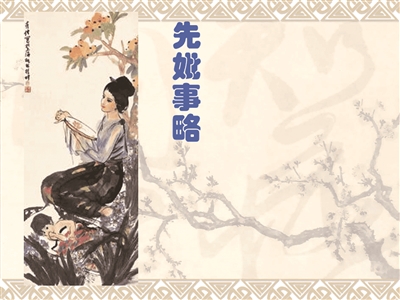□王 嘉
长期以来,归有光的散文都被誉为“明文第一”,黄宗羲曾赞其文“振起于嘉靖之盛,独领时风众势。”他写人叙事擅长以白描手法,通过自然清淡的笔法,以一二细事见之,于平淡中极见真情,“使览者恻然”。我们学过的《项脊轩志》便是其代表作之一。
在《项脊轩志》一文中,归有光以“项脊轩”为空间核心,串联起了不同时期不同的人物,在感叹斗转星移、家园变故的同时,抒发了对逝去祖母、母亲、妻子的怀念之情。写祖母和妻子时,归有光都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而在写母亲时,则是通过老妪之口来侧面描写的。这可能是其刻意的构思安排,或者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毕竟母亲去世时,归有光才8岁,记忆相对比较模糊。于是,自小无法享受母爱滋润的归有光,只能在老妪的追忆中填补记忆中的空缺。一句“儿寒乎?欲食乎?”,一个慈母形象就这样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关于《项脊轩志》,我在此前写过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一文中已有详尽的赏析,在此就不细表。今天,就来谈谈这篇归有光在其23岁、初为人父时所作的为纪念其母亲的《先妣事略》。
“先妣”,即去世的母亲。所谓“先妣事略”,即是一篇记录去世母亲生平事迹的小传。《先妣事略》全文不到600字,作者以平实的语言、克制的情感和高妙的技法,从三个部分记述了母亲的事迹。而这些事迹组合在一起,即便已经去世多年,一个勤劳朴实、品德高尚的母亲形象仍能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难怪国学大师唐文治评价该文:“令无母之人读之,自然泪涔涔下,真血性文字也。”
文章第一部分,简略地记录了归母的生平,交代了其生卒年及所育子女等情况。归母周桂,16岁嫁到归家,26岁不到即溘然长逝。嫁为人妇后,似乎其人生唯一的意义便只有四个字——“传宗接代”。仅在这10年期间,一个连着一个,共为归家产下7个孩子,其中存5人,早夭2人。即便在医学发达的现代,如此频繁的生育也必然会使其身体遭受到巨大的损耗,何况是技术落后的500年前,每一次的生产都如在鬼门关口转了一圈。况且所谓“生育”,这不仅仅只是生的问题,更费精力的还有育的问题。在生下小七有功之后,归母心力交瘁,哺养他也比前几个儿女更费力了。都说多子多福,在归母身上其实并不然。相反,其被古代传统生育观念束缚而受“多子”之苦。归母曾多次皱着眉头和婢女感慨因孩子太多而感到身体疲惫,并且在随后不得不采用了一个老婆子提供的据说可以避孕的民间偏方——喝下了一碗泡着两个田螺的水。“饮此后妊不数矣!”老妪似乎对此很有信心。然事与愿违,在喝下田螺水后,归母便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喑不能言”,成为了一个哑巴,且在3年后的一个冬夜万般不舍地抛下了5个年幼的孩子撒手人寰。此时,归有光并未直白地抒发自己和其家人是多么的伤心,而是开始了其擅长的白描手法,记叙了两个看似平平无奇的细节:其一,“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归母去世时,作为老二的归有光也才8岁。少不更事的孩子们根本不懂得发生了什么,看到其他家人哭,便也跟着哭了起来。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死亡”这二字背后的沉重含义,以为母亲只是暂时睡着了而已。其二,家人邀请画工来给归母画遗像的时候,让两个孩子出来给画工作为参照——“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因为这两个孩子的长相最像母亲。明明勾勒出的是一幅五儿“幼年丧母”的凄惨画面,归有光却一如既往的平淡和冷静,而在这种平淡和冷静的背后,又将人生和现实的残酷展现得淋漓尽致。
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归母娘家的情况及其为人品行。归母是一个“资雄”的大户人家的富家小姐,这也与其嫁入归家后却只能日夜辛劳,沦为生育机器的惨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后,作者从三个方面的细节来刻画母亲的品行:治生产、做家务方面,尽管归母“不忧米盐”,甚至娘家还经常派人来嘘寒问暖,送些物资,其却仍一直秉持着“勤俭节约”这一传统美德,“劳苦若不谋夕”。这里又有几个细节,回娘家省亲的时候一有空就纺棉花,回城以后又经常在微弱的灯光下通宵达旦地忙着搓麻捻线。“冬月炉火炭屑,使婢子为团,累累暴阶下”,连冬天烧过的木炭灰都要重新和成炭团,晒在台阶下。归母孩子众多,“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其都是亲力亲为,但仍能将家里打点得井井有条,“室靡弃物,家无闲人”,似乎没有什么是多余的;对待下人方面,归母是宽厚公正的,每逢娘家送来鱼蟹糕饼,全家不分主仆人人有份,所以只要听说其娘家来人了,大家都很开心。有时候,即便有佣人犯了错被归母责打了,他们也不忍心在背后说其坏话;教育子女方面,归有光这样回忆道:“有光7岁,与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归有光7岁时和堂兄去学堂上学,如遇阴雨天气,其堂兄便偷懒请假不去上学,而自己即便恋恋不舍也只能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去学堂。有时,归母半夜醒来,就催有光低声背诵《孝经》,直到背得流畅无差方才开心作罢。这些细节描写,画面感甚强,读者读之,就仿佛在亲手打开一卷夜半“青灯课子图”,而在这图中,既看到了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期望,也渗透着儿子对母亲的无尽思念……
文章第三部分介绍了归母去世后的一些情况。归母去世后不久,其外祖母也不幸病故了。尔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险些让周家惨遭灭门——本来一个有着30多口人的大家庭最后仅存外祖父和二舅。悲哉!
归母去世后11年,大姊嫁王家;归母去世后12年,归有光进入官学成为了秀才;归母去世后16年,归有光成婚,而大姊和归有光所嫁娶的,都是归母在生前所一一安排的。母亲去世后所历经的年月日,归有光都记得清清楚楚,看似平铺直叙流水账一般,实则感情深厚复杂。这种以强烈的时间意识来承载对逝去亲人的无限哀痛和怀念的类似的表现手法,我在去年年初发表的那篇《冬天》一文结尾借用过,当时我写道:“春来秋去,不知不觉中,奶奶离开已有5222天,叔叔离开已有973天,外婆离开也已有411天了……如今,陌上虽已渐渐花开,他们却永远无法再回来了。”
“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追惟一二,仿佛如昨,馀则茫然矣。”都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归有光在有了女儿成了父亲之后,思母之情,也愈加地强烈。每当夜深人静时与其妻忆及母亲短暂的一生,那一块块的记忆残片,如在昨日,但更多的往事却怎么努力也回忆不起来了。
“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都说绚烂之极将归于平淡,那同样的,平淡的累积也能铸就绚烂。在经历了通篇不动声色地娓娓道来之后,末尾这句全文仅有的直抒胸臆的感慨也就出现得顺理成章了。这与其在《项脊轩志》中结尾那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的写作手法恰恰相反,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