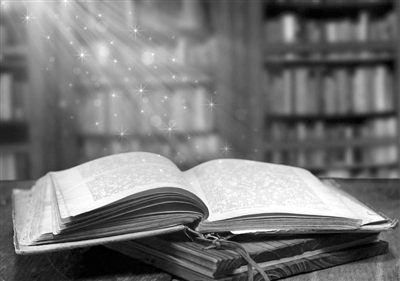一个稍具文明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即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朝毕昇发明的,被誉为人类的“文明之母”。然而,至少在1943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来中国前,我们国人没有一个知道这些事,连本国的教科书,还把活版印刷的发明,说成是荷兰人科斯特。
“谁是活版印刷术的发明者?这个问句的答语,至今尚是历史的一个疑团。但是我们大多承认,荷兰人科斯特,乃是第一个完成此术之人。”①这段话就赫然写在民国时的《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西洋史》里,此书作者陈衡哲,是当年第一批考取清华学校庚子赔款留美的女生,在美专修西洋史6年,回国后在北大执教,为中国的第一个女教授,当时连她都这么认为,何况一般的国人?
四大发明,能够冠名道姓归之于中国,实在要感谢西方的巨人。文艺复兴晚期,巨人培根于1620年完成了《新工具》一书,提到发明对人类贡献时写道:“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②。两百多年后,巨人马克思对三种发明的作用做了进一步阐发:“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③
当然,谁都不知道三种发明是哪个国家的。
1943年,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来中国考察科学技术史,发现300多年前培根所说的“三种发明”加上造纸术,原本都是中国古代发明的,这一发现公之于世,震撼了世界,极大增强了正值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李约瑟回到英国,继续收集资料,详细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陆续出版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末了,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④
这就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李约瑟谜题,谜题的答案,直到大师1995年辞世,东西方也没有找出来。
面对科技史上的活版印刷术,从西方留学归来的中国学者,与从未在中国留学的西方学者,怎么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
我国的科学技术史,在李约瑟之前,处在西方人从不关注,自己人也不在乎的境地。(我国官方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到1982年才姗姗迟来。)倒也事出有因,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一百多年间因落后总是挨打,外国人、自己人谁会重视一个落后国家的科学技术史?即使留洋的中国学者,看到了《新工具》这本科学史和哲学史上的巨著,也很难将伟大的三种发明与落后的祖国沾边。
四大发明虽是我国古人创造,然而冠名、评判及考察,皆为西方人;上世纪,本国的学术大师竟然不认得先人的发明,科学技术曾长期落在西方人后面,说起这些,身为现代中国人, 我和许多人一样感同身受,愧对先人,于是,试着想解开李约瑟的科学谜题。
我把培根、马克思对三大发明的评判和李约瑟的设问链接起来,他们分别代表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后工业时代,内容居然是联贯的,真是巨人所见略同!现以磁石为例,看它何以成为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它最早记载于公元前三世纪《管子》“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 ⑤,因它的吸铁功能,就像慈母吸引着子孙,先贤们美其名“慈石”,又因它是铁石类,才改为磁石,并磨制出了能够指示南北方向的磁石--“司南”;通过长期不断改进,到宋朝时成为应用于航海技术的指南针,航海家们依靠它犁出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15世纪,明朝的郑和曾七下西洋。指南针约13世纪传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航海家们掀起了大航海时代,便有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522年,麦哲伦率领的船队通过3年航行,第一次证实了地圆学说。一个明晰的地球概念,为21年后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横空出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这一学说是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
然而,对于磁石指南的奥秘,我国古代一般认同于方家们的阴阳五行作用;文艺复兴时期晚期,英国女王的私人医生吉尔伯特通过多年研究,揭示了磁罗盘指示南北的地磁场原理,于1600年发表《论磁体》一书,奠定了地磁学基础。
上述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磁石在中国1900年间,主要表现出技术上的使用功能,与重大的科学发现无缘;而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就成了巨人们证实、发现有关科学学说的工具、手段,自身的神秘面纱也得以真正撩开。
指南针到了西方人那里,地圆学说、地磁学说这些科学巨论的证实、发现,偏偏集中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难道是文艺复兴运动使然,她对于科学的复兴竟有如此魔力?
中世纪(约公元前4世纪-14世纪初),教会统治的欧洲窒息了人们的思想,被人称为“黑暗的中世纪”。14世纪初,诗人但丁以佛罗伦萨行政执政官的身份,担当起复兴意大利民族和文化的使命,摆脱教会的统治,他的代表作《神曲》不仅艺术成就超越了前人,主题上更是突破了教会设置的思想藩篱;另一位桂冠诗人彼特拉克更是针锋相对地指出:人性对立于神性,“人学”对立于神学,开创了人文主义,其诗集《歌集》成为打破教会思想枷锁、开启人的身心之门的代表作,他是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些人文主义作品在欧洲广泛传播,极大促进了人性和思想的解放,催生了大探索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新大陆的发现、地圆学说的证实,便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14世纪上半叶(元末明初),中国出现了推翻元朝统治的民族复兴运动,罗贯中、施耐庵两人在自己效力的农民起义集团失败后,完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古典小说,后又出现了吴承恩的《西游记》,前者借兴复汉室名义,复兴汉民族,这些作品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元素,宣扬“忠、仁、义”等儒教核心的价值观。遗憾的是,这些作品无法掀起文化复兴,当然也未能向科学复兴转化升级。
回头看看郑和下西洋,则是在海禁的大背景下奉旨出使,莫说七下,就是十下西洋,也不见得能够自主去作环球探索远航。
由此,情况渐趋明朗:中世纪之前,中国因为拥有四大发明,执技术之鞭领先于西方;而到了文艺复兴运动,西方开始执科学之鞭领先于中国。
东、西方不同的民族,在相近的时间点,一同在复兴起跑线上起步,西方因为有了但丁、彼特拉克、哥白尼、培根等巨人,他们视复兴民族、复兴文化或复兴科学的使命为己任,经过约300年文艺复兴,努力将东方传来的技术之鞭,转化为科学之鞭,带来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等各个领域的复兴,复兴这条主线贯穿于整个文艺复兴。诚如恩格斯评价文艺复兴时说的“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拥有四大发明的中国,自中世纪以来,像彼特拉克、哥白尼、培根、牛顿这样的巨人迟迟难觅身影,无法将技术之鞭转化为科学之鞭,长期在民族复兴的层面踏步。联系李约瑟的那番话,恰恰点中了中国、印度这些文明发源地的要害。
综合上述,我们不难发现:文艺复兴,实则包括民族复兴和科学复兴的多重复兴。科学既反映事物的真实表相,又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它的复兴,意味着民族复兴能够循因某种规律不断向前迈进。
文艺复兴运动结束,西方顺势迈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道,掀起了新一轮复兴,直至今天,长期领跑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
当下,我们中华民族正在复兴,同样需要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中国是怎么落后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能让巨人涌现?巨人们究竟施了什么魔法,使得中国绽放的技术发明奇葩,却在西方收获科学的累累硕果?从民族复兴到科学复兴的成功,是否存在尚未被人发现的复兴规律?……这一揽子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弄得清清楚楚,找到了准确的答案,民族复兴那个长久的心结就解开了,科学史上的李约瑟谜题自然便迎刃而解。